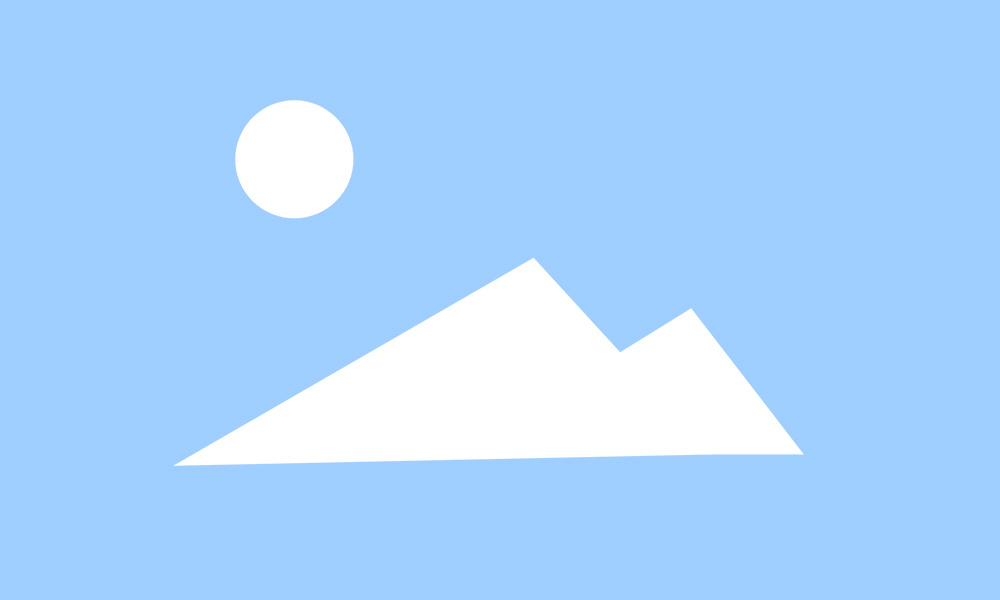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内涵、框架与测度
发布时间:
2025-10-11

作者简介 李世瑾,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研究方向:智能教育、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shijinliEdu@163.com); 顾小清,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研究方向:智能教育、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技术支持的教学创新(xqgu@ses.ecnu.edu.cn); 李睿,硕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研究方向:智能教育(lirui_0915@qq.com); 王欣苗 ,硕士研究生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研究方向 :智能教育(490513903@qq.com)。
摘要:科学评估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水平,是推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尚未有研究对此作出明确回应。为考察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综合水平和差异表现,本研究采用指数评估这一创新范式,明晰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内涵要点,设计测评框架,测度不同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研究发现:1)我国不同区域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水平从高到低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2)从东部、中部到西部的省(市、自治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呈下降趋势;3)不同省(市、自治区)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子指数存在差异,且背景、投入、过程和产出等子指数共同制约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指数水平。本研究从区域、省(市、自治区)和子指数联动等层面,提出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实践路向:缩小区域差异,积极推进优质均衡的智能教育扩张模式;加强省市合作,努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智能教育生态圈;协调子指数关系,切实优化动态发展的智能教育实践样态。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
一、问题提出
二、内涵意蕴
指数(index number)是反映事物数量变化程度的相对数(李金林等,2006),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一些指数甚至已成为预测现状的“晴雨表”(任栋等,2021)。本研究基于指数方法的思想内核,即动态持续的测评框架、需求牵引的测评过程和切实落地的测评结果(见图 1),综合研判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水平。
 (一)动态持续的测评框架
(一)动态持续的测评框架理念契合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测评的前提条件。动态持续的指数测评框架契合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逻辑。其一,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教育基础设施的智能化,还涉及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的更新升级,以在普及化的学校教育中提供适切的学习机会(曹培杰,2020)。同时,伴随智能应用的迭代优化和多元因素的复杂影响,不同区域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此背景下,动态化测评框架可动态测量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质量。其二,较之静态的指标评估体系,基于指数的评估框架更加契合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可持续内涵,可通过呈现不同省(市、自治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变化,前瞻性地布局智能教育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综上,指数这一动态持续的测评框架,为科学监测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水平提供了新思路。
(二)需求牵引的测评过程
方法契合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测评的内生动力。基于需求牵引的测评过程,有助于把控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现实水平。一方面,指数测评过程聚焦于现实发展,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确定,同样需要聚焦现实需求。相应地,基于指数的测评结果,可客观反映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差异表现,尤其通过对比不同区域指数差异,有助于制定针对性、合理性的推进举措。另一方面,指数测评过程重在对关键要素的归一化处理。它把影响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归一到同一评估标准,有助于明晰不同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各指数发展的质量水平。总之,指数这一需求牵引的测评过程,不同于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撒胡椒面式”的效果列举(李世瑾等,2022),有助于实现“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的发展目标。
(三)切实落地的测评结果
应用契合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测评的坚实支撑。切实落地的测评结果,可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抓手。首先,指数结果具备整体性特征,这种跳出静态指标体系的评估方式,能从现实的可操作视角,监测不同区域的指数水平。其次,指数结果具备落地性目的,可借助典型的、可量化的指数观测点,映射人工智能教育实践进程中关键要素的发展水平。再次,指数结果具备实用性特征。它通过关键指数撬动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有利于打造“以评促改”的实践样态。最后,指数结果具备发展性意蕴。“点—线—面—体”的指数测评结果,有助于勾勒系统化、层次化的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可以说,指数这一测评结果,可为预测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的前瞻发展提供可信依据。
三、测评框架
本研究基于“全面统整、数据易得”的指数测评思路,遵循“选取测评样本→构建指数框架→明确数据来源→确定计算过程”的操作流程,设计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测评框架。
(一)选取测评样本
为考察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指数水平,本研究基于区域性、结构性和代表性的遴选原则,分别将我国华中、华北、华东、华南、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的省(市、自治区)作为测评样本(见表 1)。
 (二)构建指数框架
(二)构建指数框架为研制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测评框架,本研究梳理了指数测评的相关模型,包括“公平—效率”视角下的教育发展指数(李慧勤等 , 2015) 、“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系统化视角下的质量评估指数(刘惠琴等,2020)、基于“起点—过程—结果”的教育时序发展指数(徐光木,2014)、基于 CIPP 模 型 (Context Evaluation, Input Evaluation,Process Evaluation,Product Evaluation)的教育决策指数(张炜,2022)。通过借鉴这些指数测评方法,同时考虑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不仅要反映发展水平,更要系统呈现变化样态的思路,本研究结合“公平—效率”和 CIPP 模型的维度,从背景、投入、过程和产出等方面构建指数测评框架(见图 2),揭示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水平的动态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背景指数聚焦于智能教育环境。智能教育环境是实现智能教育应用的支撑条件,通过赋能各类教育场景的智能功效,推动技术系统与教育系统的深度融合(刘邦奇等,2019)。具体到智能教育环境的指标构建,本研究采取简洁且关键的原则,突出人工智能教育背景的水平。
背景指数聚焦于智能教育环境。智能教育环境是实现智能教育应用的支撑条件,通过赋能各类教育场景的智能功效,推动技术系统与教育系统的深度融合(刘邦奇等,2019)。具体到智能教育环境的指标构建,本研究采取简洁且关键的原则,突出人工智能教育背景的水平。投入指数聚焦于智能教育保障。智能教育保障是有序推进智能教育实践的重要保证,主要从政策规划、资金保障、人力保障和服务支持等方面,满足智能教育应用的发展需求,并为其提供可持续的支持,从而全方位支撑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践应用(刘邦奇等,2019)。因此,智能教育保障的指标设计突出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性等特点。
过程指数聚焦于智能教育资源。这是因为智能教育资源是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重要载体(郑永和等,2023),其创建、共享和应用水平,直接关乎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落地方向和应用过程,可带动人工智能教育的重塑发展,为建设高质量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系统提供坚实保障。本研究基于过程指数的典型性、采集可行性原则,遴选智能教育资源的指标。
产出指数聚焦于教师和学生的智能教育创新水平。智能教育创新水平是对智能教育应用成效的现实考量和智慧沉淀,智能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创新型智能人才,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耦合关联,形成智能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谢丽娜等,2022)。本研究将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产出指数,落到教师和学生等关键主体的智能教育创新发展水平上,具体包括教师智能教育创新指数和学生智能教育创新指数。
(三)明确数据来源
为呈现不同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水平,数据来源的公开性和可信度是前提。公开性指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可信度指数据点能够表征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关键特征的程度。需指出的是,因我国不同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各维度数据公布时间不一,本研究结合发展现状和指标特征,以各区域最新公布的数据源作为统一标准。数据来源包括:一是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二是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电化教育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地方频道、中国知网,以及重要创新竞赛(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官网数据;三是第三方机构的统计数据(见表 2)。

 其中,背景指数数据包括不同区域的智慧教育示范区数量、首批数字校园示范校数量和“5G+智慧教育”创新应用试点项目数量。投入指数数据包括不同区域的智能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数量、智慧校园行业政策数量、智能教育发展经费、智慧教育平台名师工作室数量、智慧教育平台名校长工作室数量、智慧教育平台名师工作室和名校长工作室成员数量、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数量和设有首席信息官学校数。过程指数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为抓手,数据包括人工智能教材数量、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资源数量及教师上传资源数量、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资源浏览量和资源粉丝数。产出指数数据包括不同区域智能教育项目数量、论文数量和智能类竞赛活动获奖数量。
其中,背景指数数据包括不同区域的智慧教育示范区数量、首批数字校园示范校数量和“5G+智慧教育”创新应用试点项目数量。投入指数数据包括不同区域的智能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数量、智慧校园行业政策数量、智能教育发展经费、智慧教育平台名师工作室数量、智慧教育平台名校长工作室数量、智慧教育平台名师工作室和名校长工作室成员数量、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数量和设有首席信息官学校数。过程指数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为抓手,数据包括人工智能教材数量、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资源数量及教师上传资源数量、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资源浏览量和资源粉丝数。产出指数数据包括不同区域智能教育项目数量、论文数量和智能类竞赛活动获奖数量。(四)确定指数计算过程
指数计算过程遵循“指标数据的指数化→综合指数计算”的流程,最终合成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综合指数。
1. 指标数据指数化
指标数据指数化的关键是确定各指标权重和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通过两两比较确定同一层次要素相对于上一层要素的重要程度与数量关系,并结合专家对指标重要程度的反馈,获得各级指标的排序权重。86 位人工智能教育领域专家(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陕西、宁夏等地)参与评分。本研究运用 Yaahp 软件,遵循“确定九级评价标度→构建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分析→计算结果集结”的操作流程,确定 19 个指标观测点的权重系数(见表 2)。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环节采用如下公式,将各指标观测点数据归一至 0~100 区间,便于计算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其中,i 表示第 i 个指标,j 表示第 j 个研究对象,yij表示该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值,xi(max)表示第 i 个指标的最大数据值,xi(min)表示第 i 个指标的最小数据值。
 2. 综合指数
2. 综合指数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值,由背景指数、投入指数、过程指数和产出指数构成。考虑到各指数指标的重要程度差异不大、相关性较弱等特征,本研究采取综合指数方法,测度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水平并合成指数。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AIEDI 表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综合指数,AIDI 表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各维度指数,n、m 分别表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及各指标的分类个数,Wi、Wij 分别表示各维度和各指标观测点的权重,Zij 表示各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标准值。
其中,AIEDI 表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综合指数,AIDI 表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各维度指数,n、m 分别表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及各指标的分类个数,Wi、Wij 分别表示各维度和各指标观测点的权重,Zij 表示各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标准值。四、指数水平
(一)整体水平
我国不同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整体水平可分三个梯度(见图 3):第一梯度为领跑者。这些省(市、自治区)的总指数排名前五,且总发展指数值在 0.45 以上,依次为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第二梯度为追赶者。这些省(市、自治区)的总指数排名处于 6~20 位,且总指数在 0.29 以上;第三梯度为起步者,包括总发展指数值大于 0.0742 的 11 个省(市、自治区)。从区域综合指数看,华东地区排名第一,三省(市)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领跑者 ,其余两省的总发展指数值亦在0.33 以上。华中、华北、华东、华南、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的领头羊分别是江西省(总发展指数排名第10)、北京市(排名第1)、江苏省(排名第3)、广东省(排名第 2)、甘肃省(排名第 19)、辽宁省(排名第22)和四川省(排名第 7)。

 (二)差异水平
(二)差异水平从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排名看(见图 4),北京、广东、江苏名列前三,海南、青海和西藏的发展指数水平偏低。从全国平均水平看,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发展指数值为 0.3283,约一半处于均值以上,依次为: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四川、福建、重庆、江西、湖南、河北、云南和安徽。比较不同省(市、自治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值的差异可以发现,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值大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指数值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子指数差异
(三)子指数差异1. 背景指数
北京、广东、四川、江苏、上海 的背景指数位居前五,贵州、云南、西藏、宁夏、青海偏低(见图 5)。从全国平均水平看,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背景指数为 0.0864,17 省(市、自治区)的背景指数在均值以上,依次为:北京、广东、四川、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安徽、天津、湖南、河北、湖北、福建、新疆、山西、江西、内蒙古。未达均值的 14 个省(市、自治区)多位于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但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背景指数值处于中上水平。
 2. 投入指数
2. 投入指数山东、广东、北京、江苏、四川的投入指数位居前五,吉林、内蒙古、辽宁、青海、西藏的投入指数水平较低(见图 6)。从全国平均水平看,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背景指数为 0.1184,16 个省(市、自治区)的投入指数处于均值以上,依次为:山东、广东、北京、江苏、四川、浙江、河南、广西、江西、上海、云南、重庆、陕西、福建、安徽、山西。投入指数未达均值的 15 个省(市、自治区)分布较广,包括华中地区(湖北和湖南)、华北地区(天津、河北和内蒙古)、华南地区(海南)、西北地区(甘肃、新疆、宁夏和青海)、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和西南地区(贵州和西藏)。
 3. 过程指数
3. 过程指数过程指数排名前五的省(市、自治区)为云南、新疆、湖南、北京和山东,吉林、内蒙古、黑龙江、青海和西藏的过程指数水平较低(见图 7)。从全国平均水平看,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背景指数为 0.0541,13 个省(市、自治区)的过程指数处于均值以上,依次为:云南、新疆、湖南、北京、山东、重庆、上海、湖北、辽宁、河南、江苏、陕西、甘肃。未达均值的 18 个省(市、自治区),分别是华东地区的安徽和浙江,华北地区的山西、天津、河北和内蒙古,华中地区的江西,华南地区的福建、广西、广东和海南,西北地区的宁夏和青海,东北地区的吉林和黑龙江,以及西南地区的贵州、四川和西藏。
 4. 产出指数
4. 产出指数产出指数排名前五的为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和北京,贵州、海南、云南、青海和西藏的产出指数排名靠后(见图 8)。从全国平均水平看,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产出指数为 0.0694,15 个省(市、自治区)的产出指数在均值以上,依次为: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北京、福建、四川、河北、重庆、江西、广西、辽宁、宁夏、内蒙古和甘肃。未达均值的 16 个省(市、自治区)分布于我国七大地区,包括华中地区(湖南、河南和湖北)、华北地区(天津和山西)、华东地区(山东和安徽)、华南地区(海南)、西北地区(陕西、新疆和青海)、东北地区(吉林和黑龙江)、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和西藏)。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指数评估范式,刻画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现实水平,得到以下结论:
(一)华东地区的综合指数遥遥领先,其次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
可能的原因是:其一,华东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山东,较重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践落地,如采取协同推进的系统化思路,统筹区域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背景、投入条件、实践过程和应用成效,充分汲取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共同体的经验做法(丁世强等,2022)。其二,华南、华中、华北和西南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多为追赶者。他们的智能教育背景指数和投入指数,多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对如何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过程、如何规模化落实智能技术与教育应用的深度融合等问题,尚缺乏系统化的思考、行动和干预,故综合发展指数水平不高。其三,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受智能教育资源和智能教育应用保障等现实条件的约束,背景指数和投入指数水平偏低,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抑制了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过程和产出指数,进一步回应了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多为起步者。综上,我国不同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整体分布样态,体现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依赖”效应,即某一区域得益于前瞻的智能理念、充足的教育资源和丰富的应用实践,其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优势也随之形成“惯性”而被锁定下来。
(二)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依次呈下降趋势
具体来看,处于均值以下的省(市、自治区),其指数与均值的差距处于 0.9~4 倍之间,尤其是排名第一的北京,约是排名第 31 位的西藏的 8 倍。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较之中部和西部(市、自治区),东部省(市、自治区)更加重视“领跑省(市、自治区)”的优秀经验,包括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背景、投入保障、应用过程和产出效果等的特色做法,同时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制定了适切、落地、可操作的实践方案,故发展指数水平较高。二是源于“技术—教育—社会”联动融合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变革并不能随着技术和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发生(殷丙山等,2017)。在此情境下,东部省(市、自治区)发挥“领跑省(市、自治区)”的优势功效,组建人工智能教育研究联盟、打造研究与实践共同体(顾小清等,2022)。综上可知,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从来不只是某省(市、自治区)的事情,它依赖于彼此协作和联动。因此,发挥各省(市、自治区)“智能联动”的资源流通和经验共享优势,有助于缩小各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差距,打造高质量且均衡的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新形态。
(三)子指数差异
1)17 个省(市、自治区)的背景指数处于均值以上,较重视智能教育场景的多元化建设。背景指数位居前五的北京、广东、四川、江苏和上海,在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过程中,基于智能化、交互化和集成化原则,搭建了丰富的“学、教、管、评、研”智能应用设施体系,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背景指数水平更高。这也表明,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背景指数,取决于省(市、自治区)智能教育场景的丰富程度。这是因为,智能教育场景愈加丰富时,智能场景的叠加、复制、连接等功效愈加显著(袁凡等,2022),也越能够满足智能服务中人机协同的适切性需求,更利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深度融合和落地实践。相应的,这些省(市、自治区)的背景指数排名也较靠前。可以说,背景指数的高低正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环境阈”的表征。
2)16 个省(市、自治区)的投入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可能与智能教育投入的政策、资金、人力和服务水平相关。政策支持层面看,高投入指数的省(市、自治区),通过制定智能人才培养计划、建设智能教育智能实验室等可操作和可落地的政策举措,有助于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切实落地。资金保障层面看,经济发达的省(市、自治区),拥有更多的智能教育财政保障,这利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可持续发展。人力保障层面看,高投入指数的省(市、自治区),具备更加完善的发展机制和保障制度,如浙江省建立了首席信息官职务保障制度,设首席信息官的小学 2748 所、初中 1568 所(浙江省教育厅,2022)。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该省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引领化和科学化。服务支持层面看,高投入指数的省(市、自治区),可借助人工智能产业链、人工智能教育机构等服务,满足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差异化需求。可以说,投入指数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条件阈”的映射。
3)13 个省(市、自治区)的过程指数处于均值以上,这可能是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建设、共享和应用水平差异所致。智能资源建设层面看,过程指数排名靠前的省(市、自治区),倾向于从实践视角出发,建设能够指导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落地的实践资源,同时关注资源建设过程的优化和迭代环节,有利于部署优质、多元的智能创新资源。智能资源共享层面看,过程指数排名靠前的省(市、自治区),愈加重视智能教育资源的汇聚整合和优化利用,利于获得“领跑者省市”的智能教育实践经验。需指出的是,若要实现智能教育资源的长期优质共享 ,资源共享的适应性效率是关键因素(苏珂 ,2018)。智能资源应用层面看,过程指数排名靠前的省(市、自治区),更加重视对智能教育资源的系统评估和动态更新。实时监测智能教育资源的建设质量和应用效果,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过程的效益最大化。可以说,过程指数的高低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过程阈”的反映。
4)15 个省(市、自治区)的产出指数在均值以上,且背景指数、投入指数和过程指数也较高。这说明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产出效益,是智能背景、智能投入和智能资源等协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只有科学调控影响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才能最大程度地激活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时,当背景指数、投入指数和过程指数较高时,各省(市、自治区)才能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驱动方式,系统优化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并从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治理视角凝练前瞻且针对性的干预举措,从而达成合理预期的实践效果。综上,产出指数的高低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结果阈”的体现。
六、实践路向
由于不同区域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和子指数水平均存在差异,本研究提出了我国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向建议。
(一)缩小区域差异,积极推进优质均衡的智能教育扩张模式
我国不同区域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水平,呈现领跑者、追赶者和起步者的梯度态势。如何缩小区域差异,推进优质均衡的智能教育扩张至关重要。一方面,基于“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这一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现实,我国应面向各个区域制定差异化人工智能教育顶层政策规划 ,具体可参照政策工具框架(王毅等 ,2023),结合各区域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水平和目标规划,合理协调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劝告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的占比,充分发挥各区域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的现实价值。例如,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偏低,制定政策时应向系统性变革工具倾斜,通过系统层面重组资源和权力,推进人工智能教育政策价值的最大化落地。这一思路的可行性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已经得到证实(蔡旻君等,2019)。
另一方面,鉴于我国东部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多属领跑者,我国应充分发挥这一地区的智慧辐射效应,从理念和过程层面,带动其他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提升。思想理念层面上,各区域应充分领悟“技术现象学”的意蕴(韦妙等,2020),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情境下的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面向不同区域分层探索优质均衡的智能教育扩张模式。行动过程层面上,各区域应遵循“分类推进、短板优先”的原则,结合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背景指数、投入指数、过程指数和产出指数,分析这些维度指数的投入比重,加强治理过程的精准倾斜,同时需要明确具体目标达成的时间节点,并根据各阶段的现实表现,因地制宜制定短板补齐策略。
(二)加强省市合作,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智能教育生态圈
鉴于不同省(市、自治区)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的差异,我国应从智能共享机制和智能流通平台等方面,加强各省(市、自治区)的协同合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智能教育生态圈。其一,建立智能共享机制,即参照信息传播 SMCR(Source Message Channel Receiver)模型(南国农,2005),分别从信源、信息、信道、信宿等环节,共享智能教育创新经验。其中,信源是智能共享的源头,通过建立“智能专家层—智能教师层—智能教育企业层”的群智联通机制,打通各省(市、自治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协同方式。信息是智能共享的传递形态,借助需求导向的设计流程,助力各省(市、自治区)群智联通的体验感和效能感。信道是智能共享的方式,相关部门可参照各省(市、自治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及其地理位置和实践特色,组建“起步者→追赶者→领跑者”的进阶联盟。信宿是智能共享的监管规范,教育工作者需定期评估、反馈和更新人工智能教育协同发展的监管机制,形成“证据导向”的智能共享策略。
其二,打造智能流通平台。我国已经形成了国家级、省市级、区县级和校级的智能教育平台体系(祝智庭等,2023),可进一步基于前期的智慧沉淀,采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思路,打造面向各省(市、自治区)的智能流通平台。这包括在纵向层面以多级贯通的流通方式,实现国家级、省市级、区县级和校级智能教育平台的动态优化,如国家级、省市级和区县级平台,既能够从下一级平台遴选优质的智能资源,又可以采用第三方接口,实时汇聚特色化的智能资源;横向层面以多维融合的创建方式,联通国家级、省市级、区县级和校级智能教育平台的资源,同时避免重复性、大而虚的口号式建设,发挥各级各类平台的功能和作用,如国家级平台重在示范和引领,省市级平台重在汇聚特色化的智能资源,县级平台重在精细化的智能管理,校级平台重在鲜活化的智能实践。
(三)协调子指数之间的关系,切实优化动态发展的智能教育实践样态
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是背景、投入、过程和产出等子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若想从根本上改观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现状,摒弃原有的割裂式做法,采用系统化思路协调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各子指数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切实优化各省(市、自治区)的智能教育实践样态。
这需要构建“背景—投入—过程—产出”四维指数协同发展的调控机制,保障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1)采用动力系统仿真过程(胡艺龄等,2022b),通过模拟不同省(市、自治区)的背景指数、投入指数、过程指数和产出指数之间的动态关联和影响程度,捕获各子指数协同发展的平衡点,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规范→设计→实践”的良性循环圈。2)关注“背景—投入—过程—产出”四维指数的发展规律,探索具有实践价值的操作抓手和各子指数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时间和空间层面明晰各子指数发展的协同路径,保持不同省(市、自治区)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发展的适度张力。3)拓展“背景—投入—过程—产出”四维指数的落地抓手,强调“宽度”层面的要素丰富,也重视“深度”层面的路径创新。例如,不同省(市、自治区)在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实现补偿性增长后,应协调各子指数的投入力度和发展顺序,最大程度地维持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稳定状态;采用社会性实验方法,记录、描述和研判“学、教、管、评、研”等智能应用的前瞻性举措,并据此创建真实的、虚拟的、元宇宙式实践场域,全方位助力人工智能教育生态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教育实践质量是其落地推广的效果考量。本研究遵循“选取测评样本→构建指数框架→明确数据来源→确定指数计算过程”的设计流程,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市、自治区)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指数开展测评。研究不足在于:一是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结论可能受到指数情境的影响;二是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远比涉及的指标及其关系更复杂,需要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思路。未来,研究团队将持续推进以下工作:一是丰富潜在变量的数据来源,并从区域层面、省(市、自治区)层面和子指数联动层面,分析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问题和成因;二是引入更多实践变量,并采取人工智能教育仿真的实践范式,对我国不同区域的人工智能教育规划布局进行优化调整,推进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声明
本刊投稿网址:https://openedu.sou.edu.cn,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